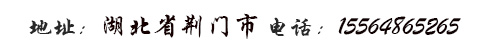贵在行走丨南迦巴瓦雪峰就在头顶封面新闻
|
北京哪些痤疮医院好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_9306283.html 南迦巴瓦峰 李贵平文/图 两年前我从拉萨旅游回来,心头挥之不去对西藏的眷恋,决定另找机会去雅鲁藏布大峡谷走一趟。年10月下旬,我腾挪出一周时间,从成都飞赴林芝完成这一冒险的宿愿。 在林芝头两天,我匆匆结束了在鲁朗林海、巴松湖、卡定沟瀑布、比日神山的采风后,用了近五天徒步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其间遭遇险情,吃尽苦头,也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 大自然中的“最后秘境” 全长近公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的秘境”,许多险峻地段至今无人涉足。我的大峡谷徒步之旅,是从林芝多雄拉山下的派镇开始的。 那天傍晚,我从林芝坐车来到派镇。第一晚,住在结巴村多登家庭客栈,50元一间,小阁楼。 结巴村四周雪峰峻峭,雪峰下是风化的砾石和黄沙形成的堆积层,起伏有序,沟壑纵横。村子只有一条独街,藏式民居错落排列。这些民居,有的是用石头修建,有的是用木材修建,有的是用砖修建,多就地取材。次日清早,我带着相机想在村里拍点什么,大多关门闭户,远处的雪峰还寂然沉睡,在淡蓝色的晨曦中微微发光。村子里,“起床”最早的是那些猪、牛、羊,它们站成一排横在路中间,鼻子哼哼像在密谋开会。最霸道的牦牛走动时,它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儿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似乎在提醒屋子里的人们:“懒虫,该起床啦。” 离开多登家,走在一段坡路上,忽然感到有些胸闷。当时我背着10来斤重的旅行包,最拖后腿的应该是佳能5D3单反相机、3个镜头和单脚架。 眼下,雅鲁藏布大峡谷浸淫在绵绵秋雨中,群山迷蒙,田畴、房屋影影绰绰,山下是蜿蜒而来的雅鲁藏布江,涛声隐隐可闻。 我正怨运气不好,不料很快变天。东边,最先露开一小片淡蓝色,渐渐地,阳光穿过一层厚云透射下来,光芒越撒越宽。近处的山峦呈翠绿色,稍远米黄色,更远淡青色,渐次晕染开来。很快,寂静的大峡谷,又现出通天透地的干净明亮。 一过中午,整个峡谷经太阳之手全都换上绚烂的秋装:层林尽染的植被、淡绿清澈的江水、巍峨洁白的雪山,低头吃草的牛羊,手持转经筒的老人……扑面而来。 下午两点过,我来到一个叫岩旁村的地方。远远看去,一处宝塔形经幡吸引了我的目光。几头苍鹰在上面徘徊。路过的藏族汉子说,那里是岩旁村树葬天台,当地人视之极为神圣。树葬是大峡谷地区最古老的藏族葬法,就是把死者置于深山或野外的大树上,任其风化,让亡灵超度到高远的神山进入极乐世界。 沿着古道往下游走去,许多地方泥泞难行,我两次栽倒,满是是泥,十分狼狈,但顾不上清理,又走。天上突然变色,乌云铺天盖地,似乎要直直地压下来。四野一片死寂,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连房屋也越来越少。我有点恐慌了。 独自徒步也有好处,边走边玩。峡谷里,哪怕是毫不起眼的花木流云,在我镜头里都别有意趣。 路上,我遇到的主要“朋友”是牲畜。一头头黑色的牦牛不时从灌木丛、青稞地走出来。看见我后,有的很客气地绕着走过,有的如交警瞪眼甩头令我不得占道。我想起前几天在尼洋河畔遇到的那些牦牛,全都那么牛逼,遇车从不让道。但牦牛也有抓狂的时候,它身上粘着嗡嗡嘤嘤比蚂蚁还密集的牛虻,这些牛虻有着死磕到底的钻研精神,对牛皮长驱直入,猛蛰死咬,吃饱喝足。 就像被铁扇公主钻进肚子折腾的孙悟空,牦牛无论怎么跺脚打滚,都摆脱不了牛虻的百万雄兵,它只好经常跳进江里去“透口气”。 头顶上的南迦巴瓦峰 徒步雅鲁藏布大峡谷第一天,下午五点,我来到索松村一名叫普布的工布族藏家。群山苍凉,烟雨蒙蒙,普布家的院子显得特别袖珍。院前种着四五种颜色的格桑花。几只小鸡在花丛里向我点头致意。 普布是个三十岁的藏族青年,他有个两岁的女儿叫卓玛。可能很久没看到陌生人,小卓玛怯生生看着我,在沙发上爬来爬去,很快嘟起小嘴儿朝我装怪相。 喝着普布家家的青稞米酒,吃着青稞饼、糌粑和老腊肉,烫个脚,在窗外清风的催促下很快入睡。我想,那一晚,除了不远处雅江的惊涛声,就只有我梦中的鼾声吧。 第二天早上,吃点东西又开走。雾锁山腰,草地上,十几头猪儿呈一字阵型跑来,其中一头黑色小猪,顽皮地将它的两只前蹄儿搭在母亲的屁股上,撒开后蹄跟在后面跑。这群猪刚想回自己的猪圈,忽然,远处啪地射来一粒弹弓,射在领头母猪的肥肚子上,母猪一声嚎叫,肉嘟嘟的嘴朝后一扬,又率队跑回草地,老老实实自己觅食。 一路上,变幻莫测的雅鲁藏布江时而狭窄奔腾,状若蛟龙,时而宽广平缓,形似巨镜,让人目不暇接。那天中午,我来到一个叫赤白村的山谷里,站在山腰忽然看到这是一处拍摄江景的好地方。是的,脚下那一道“拐弯”处在我16~35mm镜头下完整地现出S型。 人们平时在画报上看到的那张著名的“大拐弯”全景图,一般游客是看不到的。它位于多雄拉山脉最北端的阿布拉雄山脚下,除非你冒险请山民带路跋涉三四天,找到那一处终年积雪的绝壁上。 黄昏,我站在断崖望去,群山迤逦,最后的斜阳穿过云层射出几道光柱,将巍巍多雄拉山峦照射得凌厉硬朗,阴影深邃,让我感到人心在大自然面前的纯净迷茫。 当晚,我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子住下。依然很冷,摄氏三四度,屋顶披霜,寒风阵阵,我从包里拿出毛衣秋裤套在身上,才慢慢睡着。 次日早上,我走到半山腰。此时的大峡谷若明若暗,远处,南迦巴瓦峰更是云深不知处。 忽然,一阵疾风咆哮而来。这阵风,经长长峡谷的推送格外凶猛,也格外刺骨。好像它不是吹来的,而是被孤独的神灵发怒吐来的。我被吹得睁不开眼,身子晃荡,脚下一晃,差点从百丈高的山腰栽下去,山下就是恶浪滚滚的雅鲁藏布江呢。一瞬间,我右手的登山杖下意识一撑,左手抓住葛藤,才避免倾崖之灾。我吓得直冒冷汗。 “看,南迦巴瓦峰出来啦。”这时,我接到普布从老远打来的电话(居然还有信号)。我一阵惊喜,望望天空,气咻咻跑到高处。 海拔米高的南迦巴瓦峰,被《中国国家地理》称为“中国最美山峰”。这座山峰平时的神秘莫测,也让无数人哭笑不得。曾有探险家这样描述:“仅是转眼,漫卷的云烟又遮盖了她,欲再看时,却只见天空流云如织,云下群山含羞”。很多人盛兴而来,抱憾而归。 现在,我运气真好。远眺,南迦巴瓦峰终于慢慢从流云里现身。她的姿容,起初如羞答答进城打工的乡村少女,隐隐露出一截,过十来分钟又露出一截。很快,四五道山峰终于在阳光的映照下,傲然凸现。她晶莹剔透,银白的光芒与太阳争锋,她的峰尖直刺云端,令人仰视,心生膜拜…… 此时我觉得,伟大的南迦巴瓦峰简直就是为我这孤独的驴友绽放的,她就在我的头顶,她一定特别眷顾我并照亮我未来的旅行之路。 我面朝银峰,心里默默向它致敬,泪流满面…… 失恋女孩的“阳光疗伤” 很久以来,雅鲁藏布江对我来说一直是条神秘的大江,它带着天外的野性和烈日般的凌厉,从海拔米以上的喜玛拉雅山中段发源,自西向东奔流,一路劈山钻峰,滚滚涛涛,奔若惊雷,经墨脱县巴昔卡蜿蜒流入印度。现在的游人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大多选择乘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行约20公里,走马观花看看“盆景”。 徒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路上,我当然也遇到一些驴友,很多人是一脸嫩稚的八零后九零后。他们来来往往,犹如天上的白云,带着被阳光激发出来的纯洁,在风的推送下不期而遇,相互交流,依着各自的轨迹融入新的天地,再难重逢。 徒步第三天中午,我遇到两名漂亮女孩,她们自称在大峡谷转了整整六天,终于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算是完成一道神圣的仪式,也诠释了一个冥冥中非得要弄清楚的人生难题。现在,两名女孩准备离藏回家。 我喜欢在旅游的邂逅中读到一些故事。 那天,我们坐在草地上闲聊,高原的阳光将两位女孩的脸晒得红扑扑的。 穿紫色毛衣的那位窈窕姑娘姓朱,深圳某高校大四学生,兼职舞蹈演员。前不久她被男友踹了——小鲜肉爱上大自己二十岁的证券公司御姐。御姐掏出一张银行卡,像《教父》里的马里奥扔了句“我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钱”,硬是将他从小朱身边撬走了。小朱觉得天都塌了,她哭着一个人踏上去拉萨的火车。小朱身边那位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是她的闺蜜,专门赶来陪她的。“妹儿说她进藏后看不到南迦巴瓦峰,就不回深圳,就跳江。丫头傻吧!”这位善良的闺蜜笑着说。 道别时,我看到小朱的眸子里闪烁出最美山峰般的莹洁之光,青春的脸庞在阳光下更显娇媚。她伸伸手臂,在草地上一个纵跳,空中做了个拥抱太阳的动作,长腿儿轻轻落在草地上,发出一声清响,一如指尖触动在《菊次郎之夏》的钢琴乐键盘上。我知道,小朱姑娘是想跳出一个生命的高度。 下午四点过,我走到赤白村附近,远远看到,一条瀑布从南岸陡壁上跳荡下来,它宽约1米、长约80米。我后来查看资料,这是大峡谷有名的秋古都龙瀑布。 眼前又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密林,我不敢贸然穿行,等到三四名驴友来了,大家商量后结伴同行。 林子里,浓荫将昏黄的阳光筛滤得碎花满地,到处弥漫着腐木、落叶、杂草和动物遗骸的腐味儿。古道上绿苔遍地,湿亮亮的像被泼了油。我没法稳住脚步,又栽倒四五次,爬起来又走。天色越来越暗,不时有几只鹞鹰从树丫间长啸一声飞向云天。远处,各种狐狸、兔子、猴子等见到人后,也撒蹄跑过,有的跑几步还回头冲我们看看。大伙加快脚步,幸好只用了两小时就走出了林子。前方影影绰绰出现一处藏寨。地图上看,这里应该是叫加拉村。 当晚,我住在加拉村一户门巴族藏民家里。此时,我已足足走了三天多。夜幕下,流经此地的雅鲁藏布江变得特别温柔。江面很宽,至少在米,雄踞整个河谷。夜空中,弯月高挂,将四周照得渐变般隐亮。弯月投映在江面上,被缓流揉碎,呈现出鱼儿般的形状,粼粼波光就是鱼儿身上闪亮的鳞甲。 天上,密密麻麻分布着星星。这些星星颗粒之大是我从未见过的。它闪烁的光芒是在赞许我吗? 最后一晚在藏民桑珠家。我看到又有七八名不同口音的背包客走进来,攀谈后知道,他们大多数人要赶在11月底封山前走向更远的地方。当中,一名四川驴友说,他在登高拍照时不慎摔下山崖,还差点被雅江冲走,他的女朋友正焦虑地商量如何护送他去林芝治疗。还有一名湖北来的女孩,却享受了比我严重得多的待遇,被疾风吹下了山崖,左腿负伤,几乎不能走路,也打算放弃旅行。 我又独自沿来路回去。路上我租了藏民的一匹马骑着,不到两天就回到派镇。 算下来,我的这趟大峡谷之行往返近五天,约近70公里。 离开林芝机场的那天中午,炽烈的阳光在我身后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它牵扯着我对雅鲁藏布大峡谷、对这个清净之地的无尽思念。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namachenga.com/bnmcms/215418.html
- 上一篇文章: 让市民吃饱吃好每天的早餐,是这座城市的幸
- 下一篇文章: 西双版纳旅游攻略,首刷版纳建议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