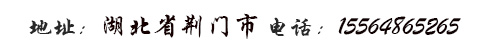明代苏州繁华程度及人口数量之考证
|
辽宁白癜风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160103/4753196.html 谈这一节,首先要明确一点,明代的苏州和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今天的苏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切不可用今天的苏州,满清的苏州去衡量明代的苏州。 首先,明朝和清朝的苏州进行对比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从著名学者李伯重的一段话说起: “到了清代,城墙外的居住区进一步扩大。康熙时,据孙嘉淦所见,‘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注释62)。不仅如此,阊门外的商业区已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延绵20里之长(注释63)。当地的虹桥毁坏后,‘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注释64)。”[1] 他这一段话是说满清时期的苏州比明代更繁荣了,居住区和商业区进一步扩大了。孙嘉淦这段话的出处注释62是孙嘉淦著的《南游记》,关于阊门和枫桥连成一片的出处,他文中对应的引文注释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遗事:‘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虹桥这段的引文注释64是:《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桥梁(实为津梁)。 表面上看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一个是引用清人《南游记》的话,一个是引用康熙时期的《松江府志》,再一个是引用清朝同治时期的《苏州府志》。 当然如果了解一点时代背景,就会有些纳闷。孙嘉淦是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他的《南游记》写于其母死后丁忧之时,其文中自叙时间在庚子秋,那就是康熙五十九年(年),而康熙《松江府志》是在康熙二年修的。 李伯重把康熙五十九年的记录放在前面,康熙二年的记录放在后面,两者之间用“不仅如此”来连接,以表明更进一步的关系,这确实蹊跷得很,难道时间在这里居然倒流了?最后一个同治苏州府志,似乎时间顺序还对得上。 我们再去查一下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结果大吃一惊!原来“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的原文明明是记载明代苏州时期的情形,和清朝半点关系都扯不上,却被李伯重张冠李戴到了清朝头上。 其原文出自卷五四《遗事下》。我把其相关背景摘录一下: “崇祯乙亥(也即年,崇祯八年),好事者倡议扩城(指扩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岳贡,锐于有为,欣然从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为不便,……钱机山龙锡贻书止之” 这钱机山龙锡,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崇焕后台,曾经担任内阁大员的钱龙锡,机山是他的号。《明史》中说他崇祯四年后就“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会周延儒再当国,尼不行。福王时,复官归里。未几卒,年六十有八”。 把他说得真是可怜兮兮的,崇祯死后才回故乡。然而从《松江府志》的这段记载来看,这厮在戍所待遇几和上宾无异,根本不是流放犯的处境,这才可能任意通信,甚至对家乡地方官员指手画脚。 康熙《松江府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崇祯八年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扩建松江府城,当时的知府方岳贡,也欣然采纳这个建议。结果触犯了当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钱龙锡就成为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给方岳贡写了一封书信要求终止修城计划。 “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就出自钱龙锡给方岳贡这封书信里的内容,其上下原文是这样的: “且市井商贾托业不同,水次贸迁,城外为便,使西城果筑,又当移居以就之。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何独敝郡偏于民穷财尽之时,倡此劳人动众之说?如民居必在城内,则自东关至华阳桥,阛阓亦四五里,南北两关,亦复栉比,又何独惜于此,而忍于彼乎?”[2] 钱龙锡反对修城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修城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大户出: “即持议者之心,亦必知必及于大户也夫。此兴无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户既穷,小民立槁,固不可为矣”。 怕要大户掏钱是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理由还不是这个,而是城外居民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利用 一旦要扩建城池,城墙所经之地的那些居民就要拆迁,这是他们坚决不干的。 还有一点就是涉及苏州的这段引文里说的了,城外从事商业贸易的市民这么多,你就算扩建了,你有办法把他们都包括进去吗?如果根本不可能都包括进去,那为什么要厚此薄彼?扩建城池又有什么意义? 正是为说明这一点,钱龙锡才拿苏州做例子,他说苏州城外的商业区,从吴阊到枫桥,绵延二十里,都没有扩建城池,凭什么我们松江就一定要扩建。 从这段记录来看,倒是可以看出明代晚期,城市人口大量溢出到城外,范围甚至比城内要大两三倍之多,已经是普遍现象了。那些扩建城池的固然是原本城内人口达到饱和,就是那些没有扩建城池,其市民溢出城外的数量甚至规模更为巨大,以至连扩城都无法包容进去,只能破罐破摔,索性不扩城了。 任何人,只要他查阅过康熙《松江府志》原文的人,都不可能搞错。所谓苏州“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只能是指的明朝时期的苏州,和清朝时期的苏州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 李伯重对康熙松江府志内容既然是如此断章取义,把一清二楚明代苏州的情形安到了满清的头上,那么他引用的同治苏州府志又如何呢?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津梁一》里确实有关于虹桥的记述,虹桥在苏州城外,若按“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城外人口密集达到这样的程度确实令人惊叹。 但问题是这段记述是谁写的,是描绘哪个时代的? 《同治苏州府志》中同样清清楚楚记载着这段话是明朝的牛若麟写的! 在卷三十三的第十页到第十一页上,虹桥条目下清清楚楚,前面是记叙虹桥历次修造记录,然后是附有前人写的关于虹桥的文字,在第十一页上,明明白白写着。下面牛若麟写的内容当中就有“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只不过李伯重还抄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负贩篓夫”,而非“窦夫”。 而牛若麟其实就是崇祯时期苏州吴县的县令,《崇祯吴县志》就是牛若麟修纂的,《同治苏州府志》不过是把崇祯牛若麟的记载抄录了一下,却不料让李伯重先生出了这么大的错误。 李伯重先生拥有一连串耀眼头衔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为该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 把这些头衔拿出来,是要吓死人的!但问题是犯下这种性质的低级错误,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不能不说相当遗憾。 为了把明清混为一谈,居然能把如此彰明昭著的明代苏州情况的记载,放到了满清头上,而且还是他专门写明清苏州对比情况的段落里,这能叫人说什么? 其实有类似行为的也远不止李伯重先生一个人。清修的地方志里的大量记录都是抄自明代典籍,明人记录,而现代许多人,往往不管不顾,拿着地方志里记录的明代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情形,当成是清时期的情况来论述。 一般人,谁有这个耐心,谁有这个心思去一一查照核对?、 大量挂着学者头衔的人,他们的对待学术的严谨程度,对待事实的忠实程度,是有很多让人遗憾之处的。 李伯重教授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必说。比如还是这条史料“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大家不妨网上搜索一下,包括一些专业期刊上所谓论文的注释里干脆把它写成出自康熙《苏州府志》了。这就是辗转抄袭,大概先是从李伯重那里抄来,冒充自己的直接引用,而非转引。然后呢一想,这明明是说苏州的情况,怎么能是《松江府志》呢,于是又自作主张改成了《苏州府志》。 回过来还是说苏州吧 满清所谓康熙盛世时的苏州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妨看看康熙的自供。在康熙二十八年(年)二月,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苏州等地后,他有这么一番议论 “又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3] 也就是康熙原来听说“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结果他亲自去巡游一看(这所谓南巡,满清官吏自然事先沿途粉饰准备过了),大失所望,苏州等地一片萧条景象,连商人贸易者也多是外地人,家给人足都做不到。于是他只好自我开解说是“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实际上如果真是习俗奢糜,那沿途各地更应该表面上是繁华热闹,花团锦簇的景象才对。这段自供可谓打了那些成天吹嘘康乾盛世的奴才一耳光。 再看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第四次南巡时候发的这两条议论,就更暴露真相了 “丁酉。召大学士等谕曰、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似觉丰裕。”[4](二月丁酉) “己丑。谕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安徽巡抚刘光美、江苏巡抚宋荦曰:向日因江南人情好尚词讼、因而倾家败业者、往往有之。迩来习俗、颇觉淳厚、词讼已减大半。生聚稍加殷繁。”[5](四月己丑) 原来到了康熙四十四年,南方民间生殖才“似觉丰裕”,生聚才“稍加殷繁”,那康熙二十八的苏杭等地,不是什么习俗奢侈的问题,而是一片贫穷萧条,在满清屠戮压迫之下人口都不多的问题! 而且就是到了康熙四十四年,大家注意康熙的用词“似觉”,“稍加”,以康熙喜好自我吹嘘的品格(最著名的如一天射死几百只兔子)来看,当时苏州等地仍旧相当穷困萧条,只不过人口稍微增多了一些而已。 至于康熙所谓的“向日因江南人情好尚词讼、因而倾家败业者”,则是颠倒黑白。造成江南人倾家败业的,恰恰是清朝残酷到极点的屠杀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掠夺,而不是什么“好尚词讼”。后来屠刀之下,人都变成驯顺奴才了,清之统治苛酷程度稍微减缓了,才人口多了一点。 我们还是切回正题,说明代的苏州吧。 明代苏州是时尚之都,工艺之都,人文之都,是全国的手工业中心,艺术文化中心,思想舆论中心,消费娱乐中心。在任何程度上,现代苏州其相对的繁华和重要程度应该是不能与明代的苏州相比的。苏州可以说是明代中国的巴黎。 关于明代苏州繁荣情形,明人记述颇多,前面被李伯重张冠李戴到清头上,实则为明代情形的“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篓夫则望洋而叹”已经能说明一定问题。 不妨再引用几条! 明代王锜的《寓圃杂记》里说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癌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駸駸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6] 明代大才子唐伯虎有一首诗描绘苏州阊门的繁荣程度: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通画难工。”[7] 关于苏州,人口之多,节日花灯烟火之繁盛,张岱曾经说过这么一个笑话: “昔者有一苏州人,自夸其州中灯事之盛,曰:‘苏州此时有烟火,亦无处放,放亦不得上。’众曰:‘何也?’曰:‘此时天上被烟火挤住,无空隙处耳!’”[8] 说天上被烟火挤住,以至后来人想放,天上都没有空隙可容纳,当然是太夸张了。但从这则故事里,也可以看出明代苏州人口繁盛的程度,以及苏州人自负至极的精神面貌。 张岱还描绘过天启时,他有一次到苏州游玩,正好碰上“士女倾城而出”男男女女都到荷花荡里乘船游玩时的盛景 “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鞋),汗透重纱。”[9] 此处提到舟中丽人应该就是闺阁小姐之类而非歌妓,所以前面特地点明是“士女”。按说这些人本应该是最注意形象的群体,而到这个时候居然“摩肩簇舄(鞋),汗透重纱”,可见人群拥挤的程度,热闹的程度。 所有的“楼船画舫”乃至渔船小船都被搜刮一空,外地远方来的游客出数万钱想要租一条船都不可能,只好盘旋拥挤在岸上。 张岱引用袁宏道的话描绘其时景象“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 这些明人描写当然只能给大家关于明代一个苏州大概的印象。我为什么给明代苏州加了这么多头衔呢?不妨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说时尚之都,也就是明代苏州引领着全国的审美品位,引领着全国的服装时髦。扩而及之,乃至各类家具,古玩,首饰,器物,全国都要看苏州的风气。 这方面明代的记录很多,不妨随便引几条,比如王士性的《广志绎》中说姑苏人: “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10] 也即凡是苏州人认为是高雅的,则四面八方的人也都认为是高雅的;苏州人认为是庸俗的,其他地方的人也都跟着认为是庸俗的。各种器具的审美品位全都由苏州人来引领,凡是苏州名家制造的器具,不惜金钱代价也要想法设法获得。 张翰的《松窗梦语》中说: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於富侈者争趋效之。”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11] 也就是所有想赶时髦,想比阔气的人,都以苏州为榜样。都认为苏州制作的服装样式才是华丽,不符合苏州样式,那就不好看。苏州制作器具才是美观的,否则就不珍贵。而外地人的越看重苏州的服装,苏州制作的服装就越加精美;外地人越看重苏州的器具,苏州制作的器具就越加精心雕琢 正因为苏州在明代就意味时尚,以至于当时人专门创造了出专有名词:苏样、苏意。据说苏意本是一个举人考进士的时候,某考官评点他的文章大有苏意,是苏东坡之意。不料以讹传讹,这个名词流传开来,成为代表苏州时髦的一名词,乃至皇宫里的后妃也都挂在嘴边。 说明代苏州是工艺之都也半点不夸张,套用句现代话来说,明代晚期苏州生产的都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其工艺制品之精美华丽,艺术含量之高,经济价值之高,不仅同时代无可比拟,就是放眼上下五百年,也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张岱《陶庵梦忆》有一段是吴中绝技,说: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12] 由简单的手工业产品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并且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有代表性,名头响亮的大师级工匠,形成了巨大的品牌效应。让一向看不起工匠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都能顶礼膜拜,赞叹欣赏,这也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高度荟萃的明代苏州才可能做到。 而且这些产品不是为观赏而观赏,都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张翰的《松窗梦语》中说: “矧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13] 所谓“锱铢之缣,胜于寻丈”,“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足见这些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之高了。 至于文化之都就更不必说了,苏州是明代的文化艺术中心,文人才子的出产比率是全国最高的地区。 比如明代江南四才子唐伯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四个人都是苏州人,比如复社领袖张溥是苏州人(其家乡是太仓,但太仓当时属苏州府管辖,而张溥的重要活动地点也在苏州,复社万人大会就在虎丘举行),明末的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还是苏州人,明末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死于清初哭庙案)也是苏州人。 明代的苏州还是当时全国的书籍出版印刷中心,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引用万历时胡应麟的话:“凡刻书之地有三:吴(指苏州)也,越也,闽也”;“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州)常(州)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又说“吴会(指苏州),金陵搜名文献,刻本玉多,巨铁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14] 可见明代苏州是当时三大出版中心之一,而且是其中出版质量最高的地方。 至于说明代苏州是“全国的手工业中心,艺术文化中心,思想舆论中心,消费娱乐中心”,这和上面几点重复,就不再一一详谈了,只针对一点谈一下。 把李伯重明清时期苏州丝织工业进行对比的说法,稍微驳斥一下,这是我以前在论坛讨论时就贴过的内容了。 李伯重说: “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要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万历29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部,织工达-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余部()。” “如前所述,明代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可能在部左右,清代中期则增至12,部以上。因此清代中期苏州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七倍” 这段话错误明显,首先是苏州城和苏州府分不清楚。明代苏州府除了苏州城本身之外,还包括了吴江、常熟、嘉定、太仓、崇明等地区。而其中吴江、常熟,嘉定,太仓本身都是相当繁荣,手工业颇为发达的城市。 “仅仅是明代苏州吴江的盛泽(这还不是苏州城!),‘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见李绍强《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一文) 而到了李伯重笔下成了‘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甚至直接拿顾炎武提到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来证明苏州机户数千人?这只能说错误明显。 他说的明中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大约在部左右,当非事实。 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是整个明代,南方的工商业比北方发达得多,而苏州府尤其是南方的工商业中心,是整个南方工商业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 明代北方也有丝织业,规模有多大呢? “根据清代的山西《潞安府志》卷8的记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登机鸣抒者不下数千家。绸品精美,有‘机抒斗巧,织作纯丽’,‘潞绸遍宇内’的说法。洪武中已在山西设织染局,主管皇绸派造。派造程序一般是‘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万历以后,也有皇帝直接诏造的情况。大致每十年明政府在潞安派造皇绸四千九百多匹。明末丧乱,受战争破坏,绸机废毁殆尽,以后清代虽然仍保留织机近二千张,但生产规模再也没有达到明朝那样的程度。”(见卫广来《明代山西手工业考察》) 也就是在明代山西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张绸机,已经超过道光时期苏州的部了 而李伯重那里,明代丝织业只会远比山西发达得多的苏州府,居然只有张? 难道说北方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张绸机,而境内仅仅吴江的盛泽一地就“衣被遍天下”的苏州府居然只有部织机?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里我还可以再补充几点,即便仅仅算明代晚期苏州城内的织机也不可能仅仅只有张。 李伯重的张是从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巡抚应天右佥御史曹时聘给万历皇帝上的奏疏里说的“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推算出来的,至于顾炎武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其依据的源头也当是神宗实录里曹时聘的奏疏。 曹时聘的奏疏其用意就是阻止万历皇帝继续征收商税,其内容本身就自相矛盾,比如前面说 “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 后面说: “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者也,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15] (这一点内容,本身也可以看出明代晚期资本家的贪婪,工人阶级的愚昧和无知。资本家为赚取更多利润,公然抗税,以罢业威胁煽动工人阶级起来闹事,对抗万历派去征收工商税收的人员。而官员则成为这些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煽风点火,放纵鼓舞)。 前面说苏州老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丝织业,或者出资当资本家,或者出劳力当工人,后面却说“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区区几千人,按照任何一种算法,连工人和家属都算进去,也不到苏州人口的五十分之一。那前面所谓的“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岂非成了笑话。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明白了。这些官员其实和那些抗税的资本家是穿一条裤子,一方面要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要说明这个税收波及影响的百姓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是把整个苏州城的百姓都牵连进去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竭力缩小当时苏州丝织业的规模,如果据实说是几十万人,那不是更说明万历征收税收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吗?整个丝织业完全是暴利行业,这样一个暴利行业,仅仅收取六万两的税银,居然还叫苦连天,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曹时聘之类的官员这种自相矛盾,前后错乱,其实和明代户籍人口胡编乱造,等是一个道理,都是要竭力压低国家征收的赋税数量。他们只有为地方和行业的眼前那点利益服务,才能博取仁德的好名声。 从一些记载来看,明代晚期仅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规模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明晚期朱国祯说苏州人“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16] 《镇吴录》有相似的记载:“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17] 蒋以化说; “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嗽嗽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旧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两资为生久矣。”[18] 这些记录甚至包括曹时聘自己的奏疏在内,无一例外的表明当时丝织业是把几乎大部分的苏州市民卷入进去的行业,而绝不可能是仅仅占据人口少则百分之一多则也不过几十分之一的数千人(算三千人好了)。 另外根据明代传教士的证词,也可以看出当时晚明丝绸产量之巨大,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 “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产丝绸,以至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着丝绸,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世界的其他地方”[19] 《利玛窦书信》里也提到: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20] 再看樊树志《晚明史》里的一些介绍: “至迟到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21] 如此庞大的本国消费量(无论贫富都穿丝绸),以及如此庞大的海外出口量(破坏西班牙本土的丝绸生产),都需要庞大的生产规模支撑才可能实现。而众多史料记载的当时明代丝制业生产的中心苏州府,苏州城内一半城市人家都从事丝织业生产,其规模只可能是以十万人以上计,而不可能是数千来计。所谓数千人云云不过是官员为了防止万历坚定收税决心的蒙骗之辞而已。 总之以上所说,都是让大家对明代苏州繁荣发达到什么程度有个基本概念, 谢肇淛《五杂俎》这样评价明代的苏州和苏州人: “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析,即穷巷下庸,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22] 李伯重引用道光苏州府志卷10的记录说: “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亦即城市人口占到全府人口的十分之八九。”[23] 明代苏州府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李伯重认为这个说法是夸大的,但从我对明代城市化水平的分析来看,这个说法可能恰恰是真实情况的记录。 清修的这类地方志本身就大量抄袭明代典籍(只要不揭露清黑暗丑恶),对这类性质的记录毫无编造夸大的必要(要编造也只能往抹黑明朝的方向去编造,而不是美化夸大明朝情况),只能是根据明代记载而来的。尤其是满清时期苏州府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城市化水平的情况下,还把这类明代记录收录其中,可见必有所本。 明代的苏州府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普及水平最高的地区,能有这样高的城市化水平是半点不必奇怪的,明代当时的农业生产率也完全能支撑这样的城市化规模。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收录的明代曹自守的《吴县城图》里说 “今生齿繁而利源薄,盖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阊阛之间,望如绣锦,丰宴华服,竞奢相高”[24] 这几乎说苏州老百姓都不务农了。 那具体到苏州城本身人口数量有多少呢? 前面钱龙锡在给方岳贡的书信里说“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25] 其实这点钱龙锡是说错了的,因为确实有人提议过给苏州扩建新城。 曹自守说: “阊、胥、盘三门外曰附郭,即以阊、盘为号,而胥固略之矣,然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往岁寇至,议者欲于城外更筑一城,俨如半壁,以附大城,乃迄无成”[26] 那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呢?《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还收录了一篇刘凤写的《阊西筑城论》,其大意是如果要扩建新城,把枫桥到阊门都包括进去,那规模实在太大了,当中还有大河阻隔,还要先修桥,再修城,实在难办(“予诘之,城固善也,必傅之大城,则两端阻以大河,必为桥,桥之又城,乃可,而桥可易为哉”)[27] 总之和后来钱龙锡反对松江府城扩建的理由一样,不是城外市民太少,不必扩建,而是城外市民数量实在太多,要扩建的话,把周边密集的工商业市民都包括进去,工程量太大,有些不切实际(主要还是阔人不肯出钱)。 刘凤给的建议是不如两端各修一城,然后互为犄角,中间的市民被夹在两城之中,遇到盗匪之乱,两城也可以提供一定保护。 但后来大概是就算修建双城,这个规模也太大,这些提议只能成为纸上谈兵,不了了之了。 总之对苏州城的人口数量的估算,已经完全不能用城墙规模来衡量了,只能按照明代大城市本身之间互相比较来估计一下。 从各方记载来看,明代的苏州是比杭州更为巨大的一个城市,既然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二百万以上,苏州城市居民(指以苏州城墙包围区域为核心,包括周边从阊门至枫桥绵延二十里的工商业市民居住地在内的区域)可能要达到三百万了。苏州可以和明代南京竞争当时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的地位 [1]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年8月第3期 [2]清康熙2年()《松江府志,圖經》,線普-55(19冊,缺圖經)第十八页 [3]《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 [4]《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四十四年二月丁酉,= [5]《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乙丑 [6]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7]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84页 [8]张岱《陶庵梦忆》 [9]张岱《陶庵梦忆》 [10]王士性《广志绎》 [11]张翰的《松窗梦语》 [12]张岱《陶庵梦忆》 [13]张翰《松窗梦语》 [14]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82页 [15]《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16]朱国祯:《皇明天事记》卷四四,矿税。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 [17]《镇吴录》万历时刊本,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 [18]蒋以化,《西台漫纪》卷四,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1页 [19]《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页 [20]《利马窦书信集》罗渔翻译,光启出版社民国75.6[.6]年出版,第47页 [21]樊树志《晚明史》上卷,第53页 [22]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23]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清史研究》年第2期 [24]顾炎武,昆山顾炎武研究会《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年出版,苏上,第页 [25]清康熙2年()《松江府志,圖經》,線普-55(19冊,缺圖經)第十八页 [26]《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上,第页 [27]刘凤《阊西筑城论》,《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上,第页 杜车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namachenga.com/bnmcdt/210608.html
- 上一篇文章: 澳洲打响第一枪全球观望,谷歌脸书不服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